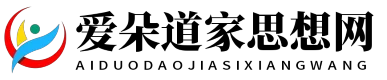刘固盛 宋元之际著名的道教学者杜道坚在《玄经原旨发挥》一书中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这里说到了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可以根据、道德、思想领域的时代需要,不断地对《老子》作出新的解释。到了宋代,在儒、道、释三教合一这种大的思想背景之下,“宋老子”也具有了与前代不同的内涵,以儒解《老》、孔老同归是该时期老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以儒家的道德学说解释《老子》,当首推王安石学派,该派王安石、王雱、陆佃、刘概、刘泾、吕惠卿诸人,都注解过《老子》,并显示出援儒入《老》、协同孔老、使老学为现实服务的共同倾向,他们的注解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下面即以王安石的老学思想为重点,结合王雱、吕惠卿等人的论述,看看他们是如何阐释老子之道德并与儒家思想统一起来的。 一 王安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人物,“荆公新学”强烈地震撼着当时的学林,推动着一代士风的转变,成为宋学发展的重要一环。苏轼评价新学的特点云:“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本)准确地概括了新学敢于打破汉唐注疏传统、提倡创新的学术精神。然而,新学不但遭到了二程、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反对,后人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全祖望撰修《宋元学案》时,序列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并云:“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述《荆公新学略》及《蜀学略》。”王梓材推阐全氏之意说:“是条叙录,兼蜀学而言之。谢山以其并为杂学,故列之学案之后,别谓之学略云。”[1]全祖望没有将新学置于正统地位,而是视之为杂学,附见全书之末,且冠之以“学略”,带有明显的贬落之意。然而,我们撇开全氏的正统偏见,单就其视新学为“杂学”而言,却是有几分道理的。杂学一字,恰恰反映了王安石之学立足儒家立场,对其他各家各派学说兼收并蓄的特点。他自己也说:“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六》,四库全书本)就是说,他读书并不囿于儒家之学,而是择善而从。我们再看以下两条材料: 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2] 学王(安石)而不至,其弊必至于佛老。(赵秉文《滏水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虽然叙述者对佛老持轻视不屑的态度,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安石之学与佛老之密切关系。荆公新学里是包含有佛老思想的,也许这就是它被视为杂学的原因吧。而对《老子》及老学,王安石尤其爱好。司马光曾说:“光昔者从介南游,介南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3]晃公武则在《郡斋读书志》里说:“介南生平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这些说法都相当有道理,王安石不但喜欢《老子》, 而且通过注解《老子》来阐述和发挥其思想观点。他注《老子》“有物混成”章云: 夫道者,自本自根,无所因而自然也。 人法地之安静,故无为而天下功。地法天之无为,故不长而万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产而万物化。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子固存,无所法也。无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4] 王安石明确指出,老子之道就是自然,它自古以固存,具有绝对性。道是“自然”如此。“自然”便是道,它根本不需要效法谁,也找不出另外的范畴可以效法,自然就是最高的规范,“道法自然”也即“自然而然”。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一解释抓住了老子之道的本质特点。然而,王安石作为一个主张经世致用、力图进行社会改革的家,注《老》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清谈自然,肯定要把这种自然之道引入到人事上,把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他注《老子》“致虚极”章云:“王者,人道之极也。人道极,则至于天道矣。”又注“谷神不死”章云:“天道之体虽绵绵若存,故圣人用其道,未尝勤于力也,而皆出于自然。盖圣人以无为用天下之有为,以有余用天下之不足故也。”天道,就是自然之道。如果完全遵循老子的自然之道,容易导致消极的无为,因此,王安石对老子之道加以改造,强调了人道、人事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固然不能改变天道,但能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继天道而成性”,“人道极,则至于人道”。人道是可以与天道互相沟通的。而圣道,“以无为用天下之有为”,正是实现了人道与天道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体现了道家的自然,又反映出儒家的进取。所以,从王安石对天道人道关系的论述,也可以看出他对儒道关系的态度。实际上援儒入《老》、儒道合流,便是王安石注解《老子》的中心旨趣。他注“不尚贤”章云: 论所谓不尚贤者,圣人之心未尝欲以贤服天下, 而所以天下服者,未尝不以贤也。群天下之民,役天下之物,而贤之不尚,则何恃而治哉?夫民于襁褓之中而有善之性,不得贤而与之教,则不足以明天下之善。善既明于己,则岂有贤而不服哉?故贤之法度存,犹足以维后世之乱,使之尚于天下,其有争乎?求彼之意,是欲天下之人尽明于善,而不知贤之可尚。 按一般的认识,老子之“不尚贤”与儒家的“举贤才”是相互对立的,但王安石作出了另外的理解。首先,他说明了尚贤的重要性,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离开尚贤的。然后,他认为老子之不尚贤,并不意味着他要否定贤能,而是希望社会恢复到太古之治,人人皆贤,也就无贤可尚了。这好比管仲临死时向齐桓公推荐隰朋,认为他能够做到“上忘而下不畔”,可托大事。所谓“上忘”,意思是自己把自己的贤能忘了。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人们就不会,也不会有尚贤的弊端。因此,老子之不尚贤的实际目的是更高层次上的尚贤,与儒家一致。此一注解也反映了王安石对老子思维特点的一种理解,即老子从反面立论而可以达到儒家正面肯定的效果。这种认识在“载营魄”章的注文中就显得更加清楚了:“孟子言其气,则谓‘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老子乃谓‘专气致柔’,何也?孟子,立本者也;老子,反本者也。”王氏认为孟子与老子立论表面上相矛盾,一立一反,实际上殊途同归。南宋叶梦得的一段话恰好可为之作一注脚:“老氏论气,欲专气致柔如婴儿;孟子论气,以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充塞乎天地之间。二者正相反,从老氏则废孟子,从孟子则废老氏。以吾观之,二说正不相反。人气散之则与物敌而刚,专之则反于己而柔,刚不可以胜刚,胜刚者必以柔,则专气者乃所以为直也。直养而无害于外,则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气,当如曾子之守约,约之至积而反于微,则直养者乃所以为柔也。盖知道之至者,本自无二。”(焦竑《老子翼·卷五》,道藏本)叶氏论述了正反相合的道理,得出了道无二致的结论,乃王注的进一步展开。 王安石不仅论证了儒道可以统一,进而认为儒学的发展离不开老子之道。他注《老子》“有物混成”章曰:“虽仁义之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于道。”但这个“道”,自然空虚,微妙难识,人们又要怎样才能效法呢?或者说,老子之道,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运用到儒家的实践中去呢?针对这一问题,王安石提出了道分本末的观点: 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4] 道之本,指道的基本性质。道之末,指道的功能作用。在王氏《老子注》中,道之本末、有无是相似的范畴,他注“道可道”章说:“道一也,而为说有二。所谓二者何也?有无是也。无则道之本,而所谓妙者也。有则道之末,所谓微者也。……是二者,其为道一也。”王氏认为道之本是自然的,万物赖它以生,毋须假借外界的力量;而道之末则与形器有关,其作用在万物成长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根据道之本,圣人可以无为无言,但根据道之末,圣人又不能无为无言。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道含本末有无,那么无为与有为是可以统一的,或者说,有为本身也是老子之道的必备内容。而王氏所讲的有为,乃是运用儒家礼、乐、刑、政四术,这样一来,儒家的礼、乐、刑、政也包含于老子之道中了。由此可见,道之本末论实际上还是为儒道合一寻找哲学上的依据,从而把老子崇尚的人道与儒家注重的人道结合起来,亦即把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经世之学结合起来。 王安石一方面吸收老子之道德为己服务,另一方面又指出老子之道的不足之处:“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预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人之为也。”[4]王氏认为,老子之不足在于唯道是称,过分强调了道的自然无为,而忽略了道在社会生活层而的功用,没有重视礼、乐、刑、政等形器方而的内容。事实上,道是体用一源,本末相依,既言自然也涉人为,所以仅言自然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形器方面的因素,充分发挥礼、乐、刑、政等社会制度和措施的作用:“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欲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天下 , 而坐求其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4]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安石注《老》之目的,是对老子之道论进行一番改造,将儒家的学说与老子之道统一起来,从而为自己的活动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他从本末体用的观点来论老子, 而最终必然要归结到现实的改革中去。”[5](P335) 二 王安石学派中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王雱,他是王安石的儿子。与其父的老学思想类似,王雱同样强调把老子之道与儒家统一起来,他注《老子》“绝圣弃智”章云: 至德之世,父子相亲子而足,今更生仁义,则名实交紏,得失纷然,民性乱矣。盖盛于末者本必哀,天之道也。孝慈,仁义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尧舜之道,专以仁义,而子以老氏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为功,而秋以收敛为德。一则使之荣华而去本,一则使之凋悴而反根。道,岁也;圣人,时也。明乎道,则孔老相为始终矣。 这段话反映了王雱老子研究的基本思想。第一,他认为如果懂得了道的微奥,则孔老实不矛盾。我们先分析一下王雱有关道的论述,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上文。他与王安石一样,以为道有本末之分:“道之本出乎冲虚杳眇之际,而其末也散于形名度数之间。是二者,其为道一也。……冲虚杳眇者,常存乎无;而言形名度数者,常存乎有。”(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大旨》,道藏本)道之本是微妙难言的,与“无”相当,道之末则体现于形名度数也即礼、乐、刑、政等社会制度之间,与“有”一致。但本末、有无并非从属于不同之道,而是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即“是二者,其为道一也”。所以从根本上说,孔、老两圣人所求之道是相同的。但为什么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孔、老又会互相抵牾呢?这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老子之言详于无而略于有,《诗》、《书》、《礼》、《乐》、《春秋》之文则详于有而略于无,然而道是有无并载,不可分离的:“盖有无者,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故非有则无以见无,而无无则无以出有。有无之变,更出迭入而来尝离乎道,此则圣人之所谓神者矣。”(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大旨》,道藏本)圣人穷神知化或详于无,或重于有,都不离道,这就是王雱所云“明乎道,则孔老相为始终”之意。他为了说得更清楚一点,还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道相当于年岁,则孔老二圣人归属于不同的季节。孔子属于夏季,王雱《老子注》序云:“自尧舜至孔子,礼章乐明,寓之以形名度数,而精神之运炳然见于制作之间。定尊卑,别贤否,以临天下,事详物众,可谓盛矣。盖于时有之,则夏是也。”这种完备的典章制度与繁华的器物文明,不正如夏季之灿烂与荣华吗?而老子则属于秋天,王雱继续说:“夏反而为秋,秋则敛其散而一之,落其华而实之,以辨物为德,以复性为常,其志静,其事简。夫秋岂期于反复乎?盖将以成岁而生物也。”物极必反,如果听任世俗之繁华激荡而不知返本,则必至物欲横流,风俗颓废,社会腐朽,所以老子便要否定它们,如秋风之扫落叶,最终返本归根,比复性为常。由此可见,孔老之相始终一如四季之相更替。 第二,王雱思想中有老高于孔的倾向。此点我们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考察:首先,王雱明确承认自己是“以老氏为正”。老子言无,言本,孔子言有,言末;孔子如夏日荣华,弄不好就会离开本根,而老子似秋天收敛,能够返本复性。当然,他并没有否定孔子,而是认为儒道不可偏举。不过,在《老子》的具体注文中,他虽立足于儒家立场,但更多的时候以道家为归趣。例如他注“天下皆知”章说:“夫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虽事而未尝涉为之之迹,虽教而未尝发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济,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颜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复朴也。”又注“民不畏死”章说:“使民逍遥乎天下之广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王雱认为,民性本来是广大流通的,但由于世教日衰,已不能使民风归朴,导致人心失控,纷争迭起,所以老子提倡无为之学,不言之教,欲使众人反常复朴,各遂性情,逍遥于天下。这种理解应该是比较切近《老子》一书之主旨的。其次,提倡黄老之政术。我们知道,到了北宋中叶,在社会表层的繁华之下掩盖着日趋激烈的和社会矛盾,因而才会发生王安石的变法运动。那么,王雱对《老子》的注释,是不是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呢?或者说,是不是准备为王安石的变法提供某些理论依据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他在注“小国寡民”章云:“老子大圣人也。而所遇之变适当反本尽性之时,故独明道德之意以收敛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朴。诚举其书以加之政,则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经》之义终焉。”即是说,《道德经》是一部治世之书,如果“举其书以加之政”,就可以“化民成俗”,使天下得以治理。这表明,王雱与他父亲一样,是主张把《老子》中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现实中去的。因此他在“道常无为”章注中明确提出:“君人者,体道以治,则因时乘理,而无意于为,故虽无为,而不废天下之为,虽不废天下之为,而吾实未尝为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尽之矣。”治国治人之道,在于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无为而不废有为,这是典型的黄老之术。我们再看“将欲翕之”章的注文: 鱼巽伏柔弱,而自藏于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圣人退处幽密而操至权,以独运斡万物于不测,故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岂暴露神灵而使众得而议之哉?尝窃论之: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知几也。夫以刚强遇物,则物之刚强不可胜敌矣。天下皆以刚强胜物也,吾独寓于柔弱不争之地,则发而用之,其孰能御之者?观夫天道,则秋冬之为春夏,亦一验矣。彼圣人者,自藏于深渺之中,而托柔弱以为表,故行万物于术内,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谓密用独化者。 老子思想中本来就包含有“君王南面之术”,王雱则在这一方面大加发挥。“操至权”、“独运斡万物”,意谓运用国家的最高权力,推行礼、乐、刑、政等儒家制度,以治理天下,控制万物。但在运用这些权术的时候,要注意策略。不能率直而为,不能以硬碰硬,而应充分吸收黄老的以柔克刚之法,“退处幽密”、“自藏于深渺之中”、“托柔弱以为表”,然后抓住时机,待势而发,最后一举取得胜利。这样的政术如果运用得好,那真是神鬼莫测,威力无穷。试比较王安石对该章的注解:“鱼之为物,深潜退伏而藏于深渊之中,而不可脱于渊。圣人之利器,常隐于微妙,而不可脱于朴也。”王安石之注虽较简单,但主要意思也是要让圣人治国的利器处于深藏不露的状态之下待机进取。可见,王氏父子的论述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也许,这是他们在当时党派之间斗争相当激烈的环境中所作出的一种明智的判断与选择。 三 分析了王安石父子的老学思想后,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应该提及,他就是王安石的同事吕惠卿。吕惠卿曾协助王安石修撰《三经新义》,熙宁七年(1074)王辞相后,便推荐吕氏担任参知政事。尽管他们两人后来产生了矛盾,但王安石变法之初,吕氏是比较坚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曾说:“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吕)惠卿与(曾)布始终不易。”(见《琬琰集删存》卷三《曾布传》)而吕氏对老庄亦颇有研究,其老学著作为《道德真经传》,内容主旨均与王安石一派相近。 吕氏认为《老子》是一部治世之书, 而非避世之文。他说: 曹参师于盖公而相齐国,孝文传之河上而为汉宗,仅得浅肤,犹几康阜。夫唯俗学,不识道真,徒见其文有异《诗》《书》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吕惠卿《道德真经传》,道藏本) 吕氏认为曹参、汉文帝用黄老之术,使国家大治,尚仅得《老子》之皮毛。如果仔细参究,其中更有深意。可世俗之士被“不尚贤”、“绝圣”、“绝学”等表面上的文字所迷惑,认为《老子》与儒学相悖,而实际上,《老子》是一部治世要典,乃“皇王之宗”,与儒家学说并不矛盾。因此,吕氏在注文中屡次提醒读者,不要被《老子》的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而要“究其微言”,体会“中有妙物”。那么,他又是怎样推究微旨,和同儒道的呢?且看以下几个例子:(一)绝学无忧。儒家提倡学而不厌,老子则绝学,这是儒道矛盾之处,但吕氏说:“夫老君神矣,何所事养,而与众人俗人为异而已,欲使为道者知如此而后可以至于道故也,然则绝学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谓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绝学无忧之意矣。”(吕惠卿《道德真经传》,道藏本)吕氏认为老子的绝学,是要去智而忘心,无为而神,以至于道。绝学就是要绝去俗学,即不像俗人那样逐物役智,以资其视听思虑。老子绝学致道,孔子学以致道,求道目的实无两样。过去儒家批驳老子的“绝学无忧”,实际上是没有弄明白其中的意思。(二)绝仁弃义。这是儒道最有争议之处,但吕氏说:“夫老君真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万物为事,而 于侯王之间如此其谆谆,何也?道以修之身为真,而以修之天下为普,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则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啬其道而欲与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义也。而学者顾见其言有绝弃仁义,则曰老君槌提吾仁义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呜呼,彼不见其所以绝弃之意,宜其不取焉耳。”(吕惠卿《道德真经传》,道藏本)儒家反对老子的绝仁弃义,而吕氏认为老子有仁有义。儒家的人生哲学和理想,可以用《大学》里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正身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概括之,反映了儒家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修身而至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而老子之道以修身为真,以修天下为普,如《老子》“善建不拔”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两者比较,可见儒道之间确实存在着一致之处,吕惠卿正是抓住了这种一致性,连结两家,使之互相贯通。(三)弃礼。儒家强调“克己复礼”,老子则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吕惠卿却说:“老君之察于礼学如此,而谓老君之绝灭礼学者,岂知其所以绝灭之意乎?”(吕惠卿《道德真经传》,道藏本)老子曾为太史,当然是懂礼的,故有孔子向他问礼之事。吕氏认为老子是知礼而反礼,因为周之末世,大制散于智慧之伪,民失其性命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孔子倡导儒学,欲求“文武周公之坠绪”,但己经无济于事了,老子身为“史官”,对这一点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所以他要否定礼乐,而推原道德,反本复始。从此种意义上讲,老子之学与孔子之传,实乃相为表里,可惜世人难以明白,徒认为《老子》之文“有异于《诗》、《书》之迹”。 四 王安石之重视《老子》,是有历史原因的。据《宋史·王安石传》,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拜参知政事后,神宗曾问他:“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从君臣二人的对话中可看出,当时人们眼中的儒学,就是经术,即汉唐以来的笺注之学,那实际上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空谈,这样的经术当然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了。因此,王安石要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找到新的理论武器,这就是把“经术”与“世务”结合起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在对儒学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他从《老子》那里找到了所需要的新鲜血液。我们再看《王安石传》中的以下记载:“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迁,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唐太宗是历史上著名的有为之君,文事武功,无不俱全,难怪这位宋神宗十分向往,但王安石却认为应该以尧舜之道为法。诚然,唐太宗无法与尧舜相比,但是,在一般儒者看来,尧舜之道是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的,只能作为一种崇高典范以供后人膜拜而已,可王安石竟用“至简”、“至要”、“至易”加以概括,这样一来,尧舜之道固然可作儒家的典范,可又与黄老“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之旨有多少区别呢?如果尧舜可成为儒道共同崇奉的帝王,那么尧舜之道与黄老之术也是完全可以沟通的。把黄老思想等同尧舜之道,足见王安石对黄老的推崇。基于这种认识,王安石便把《老子》里的大量内容吸收到了他的新学体系中,并用注释的方式阐明了儒道同归的思想。 而从老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及其学派的以儒解《老》,是老学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宋代林东《老子注》序言里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时老学研究者以儒解《老》的普遍态度:“夫子与老氏垂教,盖亦互相发明。夫子以仁义礼乐为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虚无恬淡明大道之所从生。要之仁义礼乐,非出于大道而何?而虚无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后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纯尚清虚恬淡而至于废务,有以累夫老氏也。且以道心惟微,无为而治,吾儒未尝不用老子。如所谓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未尝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则大道之与道一而已矣,特不无本末先后尔。盖所以互相发明,俱为忧世而作也。”孔、老之道可以互相发明,孔、老之书均为救世之作,这也是王安石学派的共识,此种共识不仅反映了王安石学派力图援引老子思想为现实服务的老学宗旨,而且充分反映了宋代以后儒道合流这种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宋元学案:卷九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宋史:卷三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彭耜.道德真经集注杂说[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4]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