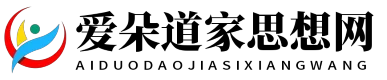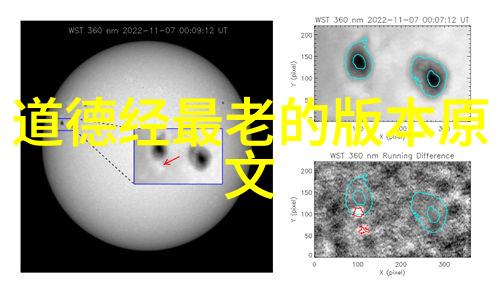黄永锋 道教的思想源头道家、医家等固有“重人贵生”的理趣和方术,道教创立以后从理论和技术两方面加以充实,从而使自身重人贵生的宗教养生观十分突出。现存最早的道教典籍——《太平经》就旗帜鲜明地展示了道门中人的重生思想。《太平经》宣称:“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天者,大贪寿常生也,仙人亦贪寿,亦贪生,贪生者不敢为非,各为身计之。”[1]“丧者为贱,生者为贵。” [2]“人各有志,各自有所念,各有所成,其计不同。各有所见,各有所出生,各自欲有所得,各知其所,心乃了然。是曹之事,要当重生,生为第一。余者自计所为。”[3]这些人寿最重的表述是道教精神气质的典型体现。为了实现长生这一目标,《太平经》的作者们以其宗教家的情怀吸纳当时之医学成就,并加以创造发挥,阐论了守一不死、为善长寿、医药护生等方面的养生理法,鲜明体现了道医的智能与特色。《太平经》作为道教的早期典籍,它重人贵生的理念及其操作方法对其后之道教医学影响深远。后世之道教养生家敷衍成说,使之蔚为大观。东晋葛洪提倡现世生活,他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4]唐代司马承祯盛赞人为万物之灵:“在物之形,唯人为贞;在象之精,唯人为灵。并乾坤,居三才之位,合阴阳,当五行之秀。”[5](《服气精义论》)宋代刘词《混俗颐生录·序》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道教重人贵生的底蕴:“天地之间,以人为贵。言贵者,异于万物也。人之所重者荣显,所宝者性命。”[6]道教典籍中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那么道门为什么如此重视人的生命? 仔细阅读道教经典,我们发现道教重视人之生命基于两点认识。首先,从生命起源观来说,道教认为人是万物之灵长者,所以应当珍惜生命。约出于唐代之《太上长文大洞灵宝幽玄上品妙经·万物造化章》云: 天地升降,冲和气成,万物皆有荣枯。尽含一气,方能变化,不论金石草木,鸟兽鱼虫,皆是天地之造化所成。于万物之中,惟人最贵,惟人是万物之首也。头圆足方,上阳下阴,皆同于天地。固天有风雨,人有血气;天有日月,人有眼目;天有万象,人有万神;天有八极,人有八脉;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地有山岳,人有骨节;地有草木,人有毛发;地有江湖,人有血脉。此者无不应于天地,人为万物之首也。若人不禀天接地,负阴抱阳,岂于天地之中,惟人动合天地造化。[7] 这段文字以人之头足、血气、眼目、身神、八脉、五脏、四肢、骨节、毛发、血脉比类天地万象,类似的又见于北宋《云笈七签》卷二十九《禀生受命部·禀受章》以及元代九华澄心老人飞集服食养生经《三元延寿参赞书》卷一《人说》。此类见解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也说明了道教养生家对人之身心与自然界的紧密联系有比较多的认识。上述几条材料中比较侧重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谈人类生命的贵重,似出于晚唐之服食经《四气摄生图·序》则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谈人的重要性: 夫理国者以养人为本,修身者以治病为先,覆载之间唯人为贵。是以《洪范》五福其一曰寿,皇天犹以为景福之最。人因元气,假以成形,受气阴阳,皆禀天地。江河淮济,五岳九州,草木星辰,触象比类,皆神明所居,各有所主,存之即有,废之即无,存之即生,废之即死。《黄庭》口为天关精神机,足为地关生命扉,手为人关把盛衰。天地含灵,皆在人之掌握,身贵若此,命岂轻哉?[8] 此引文既从气生人讲人生命之来源,但着重假借《黄庭经》说明“口为天关精神机,足为地关生命扉,手为人关把盛衰。天地含灵,皆在人之掌握”,既然这样,就要珍惜宝贵的生命,使之安康强健,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一如所谓“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9]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道经不仅从自然界对人的垂爱,也从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来论述人命之宝贵,其认识是比较成熟全面的。 其次,从父母生育来说,道教认为父母生育子女含辛茹苦,子女欲报父母恩当珍惜生命。对于父母生育过程之艰辛,元代九华澄心老人飞集《三元延寿参赞书》卷一《人说》有一段详细的描述。《人说》兼取藏传佛教、中医学、道教学说用三十八个七日讲述婴孩在母腹孕育长养的艰辛过程,即“人身岂易得哉!鞠育之恩,又岂浅浅哉!”。值得说明的是,该文的说法有的不一定与现代医学相一致,我们不能苛求没有现代医疗设备的古代医家高明到纤毫无差,而且这则材料主旨也不是科学研究,而在于表达父母生育子女的苦痛经历。《三元延寿参赞书·人说》还认为: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成就事功,所谓“既得其寿,则富贵利达,致君,光前振后,凡所以掀揭宇宙者,皆可为也[10]”说的就是这层意思。所以,飞提出:“夫以天地父母之恩,生此不易得之身,至可贵至可宝者,五福[11]一曰寿而已。……盖身者,亲之身。轻其身,是轻其亲矣。安可不知所守,以全天与之寿,而有以尽事亲之大乎。”[12]他认为为报父母养育之恩,就要重生养生。加上上文所论,人为万物之灵,应当珍惜生命,故此重人贵生成为道门教义之一就不难理解了。既然重生,那么要如何养生呢?道门养生途径众多,服食养生是重要方面,服食术中最能体现道门重人贵生情怀的是对瘟疫防治和妇幼保健的倾力奉献。 瘟疫又叫温疫、疫病、伤寒、时行等,中医认为瘟疫是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一类疾病,多由感受时行疠气导致。按今天的名词,瘟疫就是传染病,是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体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如天花、疟疾、鼠疫、麻疹、霍乱、伤寒、恙虫病、肺结核、流感、黄热,等等。在人类历史上,瘟疫曾造成深重的灾难,“在刚刚结束的20世纪,仅天花就夺走3亿人的生命,相当于该世纪发生的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3倍以上。为此诺贝尔医学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在20世纪共颁发的91次中,免疫学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类传染病防治就获奖26次,占28.57”[13],由重视察见危害之严重。在我国,商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此后,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瘟疫的鬼魅,特别在战乱和旱涝年代,瘟疫的爆发更是触目惊心。据张剑光先生统计,东汉共有大小疫病流行年份20多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40多年,元朝多达30多年,明朝跃至118年,清朝高至134年。[14]这些朝代是瘟疫肆虐的高峰期,我们现在仅以疫情稍好的宋代来考察一下瘟疫的可怕后果,据《宋史》卷六十二《志第十五·五行一下》记载: 淳化五年六月,京师疫,遣太医和药救之。 至道二年,江南频年多疾疫。 大观三年,江东疫。 建炎元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 绍兴元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三年二月,永州疫。六年,四川疫。十六年夏,行都疫。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 干道元年,行都及绍兴府饥,民大疫,浙东、西亦如之。六年春,民以冬燠疫作。八年夏,行都民疫,及秋未息。江西饥民大疫,隆兴府民疫,遭水患,多死。 淳熙四年,真州大疫。八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众。十四年春,都民、禁旅大疫,浙西郡国亦疫。十六年,潭州疫。 绍兴二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三年,资、荣二州大疫。 庆元元年,行都疫。二年五月,行都疫。三年三月,行都及淮、浙郡县疫。 嘉泰三年五月,行都疫。 嘉定元年夏,淮甸大疫,官募掩骼及二百人者度为僧。是岁,浙民亦疫。二年夏,都民疫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三年四月,都民多疫死。四年三月,亦如之。十五年,赣州疫。十六年,永、道二州疫。 德佑元年六月庚子,是日,四城迁徙,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天宁寺死者尤多。二年闰三月,数月间,城中疫气熏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15] 《宋史》仅记录那些比较大的疾疫,但单单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中,我们仍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宋代瘟疫持续的时间长,传播的面积广,死亡的人数多。在我国古代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背景下,人口众多意味着农业发展,手工业兴旺,商品流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祥和。反之,瘟疫造口锐减,各行各业相应萧条,经济发展停滞甚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政局因而动荡不安。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非典”危机和禽流感事件,让人们感受到传染病的防控是极端艰难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古代,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卫生医疗条件比较差,所以,瘟疫的流行总是牵动上上下下的神经,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各界往往共同谋划、献策献技来防治这些灾害。道教秉承“重人贵生”之教义,创立伊始就特别关注用符水治疫,甚至可以说汉末魏晋南北朝道教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就是对瘟疫流行的积极回应。从东汉到明清,历代道医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努力探索辟瘟和治瘟之方法,对当时百姓的生命健康、社会的安定发展做出不菲的贡献,其中许多措施在今天看来仍有实用价值或借鉴意义。 通过查考道教典籍,我们发现道教防治瘟疫的办法有服食丹药、服食神符、信道奉神,焚香诵经、佩符诵咒、举行醮仪,等等。下文我们仅讨论服食家采取的辟瘟、治瘟方法,这方面有代表性的道经如东晋葛洪《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唐代孙思邈《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唐代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唐宋间《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两宋之际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宋元《太上灵宝净明天尊说御瘟经》、明代《灵宝无量度人上经》、明代《急救仙方》,等等。 葛洪是东晋著名道医,其著作《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中有关传染病防治的内容主要在卷一至卷三,其中治卒中五尸方、治尸注鬼注[16]方、治卒霍乱诸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治时气病起诸劳复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治寒热诸虐方最为重要。关于葛洪在传染病学上的成就,厦门大学盖建民教授等学者已做过到位的研究,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葛洪首创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狗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到19世纪法国巴斯德才证明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葛洪《肘后备急方》书中对天花(“虏疮”)病状、发病过程以及传染性的记载是医学史上最早的;他对结核性传染病以及沙虱病(恙虫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17]葛洪防瘟治瘟的成就还可以从《肘后备急方》卷二中一段综论瘟疫的话中加以体会: 凡治伤寒方甚多,其有诸麻黄、葛根、桂枝、柴胡、青龙、白虎、四顺、四逆二十余方,并是至要者,而药难尽备,且诊候须明悉,别所在撰大方中,今唯载前四方,尤是急须者耳。其黄膏赤散,在辟病条中,预合,初觉患便服之。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风,使人骨节缓惰受病,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道术符刻,言五温亦复殊,大归终止,是共途也。然自有阳明、少阴、阴毒、阳毒为异耳。少阴病例不发热,而腹满下痢,最难治也。[18]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葛仙翁对瘟疫治疗方的收集是详备的,“凡治伤寒方甚多”,他知晓整理的有“二十余方”;但是葛洪考虑到普通人药物难于尽备,抉择了急需的方子四个,方便常人使用。另外,葛洪对瘟疫的病机、证候、病传有独到的认识,精辟地指出伤寒、时行、温疫“源本小异”,利于时人后学辨证施治。葛洪在传染病学上做出突出的贡献,今人称颂他为“中国古代的传统病学家”并非过誉。 唐代药王孙思邈在传染病防治领域也是成就卓著,明版《道藏》所收《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所收伤寒方起于卷二十九止于卷三十五,共分十六类,凡243个处方,比起葛洪,孙思邈收集之伤寒方数量多,真是网罗巨细。天津市王顶堤医院王秀菊先生研究发现孙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染病史料,她认为孙氏准确指出痨瘵之病[19]位在肺,率先对麻风病作专论,辨析阴阳毒病因、证治及其预后,探研痢疾、霍乱之病因证治,对传染病学所做的杰出贡献。[20]孙氏对于瘟病的病因、病症做出了独到的总结,那么其处方的防治效果如何呢?以屠苏酒为例。孙思邈用大黄、防风等配制成的屠苏药酒来“辟疫气令人不染瘟病”,其配制方法如下: 屠苏酒,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之方: 大黄(十五铢) 、白朮(十八铢)、桔梗、蜀椒(各十五铢)、桂心(十八铢)、乌头(六铢) 、菝葜(十二铢)、右七味 这种屠苏酒确实对预防瘟病相当有效,“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以至于后来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把屠苏药酒当作过节的必备品。宋代王安石诗《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苏轼《除夕野宿常州城》诗云:“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生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两位大文豪,心境不同,但对屠苏酒的钟爱之情却相似,可见屠苏酒的影响多大!由于屠苏酒的确能够防病除瘟,所以后人在纪念孙思邈的药王庙上题写“屠苏”二字,以示追思感激之意。 道教服食养生者还通过服食神丹以及服食灵符来防控传染病,如宋元净明派道经《太上灵宝净明天尊说御瘟经》宣称瘟疫疾病由鬼神主掌,以惩罚行恶之人和修道及其眷属不如法行善者。世人如果去恶从善并施用太上灵宝净明天尊降授之御瘟神符、赤散雄丹,可抵御瘟毒疫气。[22]道教认为瘟疫是神鬼降罪,用于扬善止恶。基于这种神学信仰,道教服食者也用符箓驱瘟,符箓派道士造作的大量符经中有许多辟瘟治瘟符,如唐朝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卷上除了理百病符外,还有专门的瘟疫符、伤寒符、寒热符各多种,该书卷下则有治下痢、治霍乱、治淋病、治疟疾诸符各多种。[23]宋代路时中编《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卷十三《斩瘟断疫品》收有“天师逐瘟符”、“太上斩邪断瘟消疫神符”、“太上慈悲救苦共卧不染病炁密符”、“太上治传染斩瘟鬼符”等服食符。[24]宋代《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下也有辟瘟服食符多道。[25]这些神丹与灵符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玄密的色彩,但它们一般采用雄黄、朱砂制成,用作消毒药品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瘟疫的流行造成生灵涂炭,道教服食养生者重视辟瘟治瘟鲜明反映了道门的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在中国古代,瘟疫的严重后果在于人口锐减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妇女、儿童身心健康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人口的数量多少,还与人口质量高低休戚相关,这种论断是有现代医学研究根据的,现代医学认为孕妇之健康对于胎儿茁壮成长极为重要,儿童时期之养护对孩子日后健康亦意义重大,所以历代医家十分重视妇幼保健,道医也不例外。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他说,“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也”(《孙真人备急千金药方》卷八)[26],在孙思邈看来妇人和小孩在延续人类生命上负有特殊的使命,因此他在《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中将妇科、儿科列在诸科之首,凸显了妇儿科的头等地位,为小儿、妇产建立专科创立了条件。明版《道藏》收录之《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二至卷七是妇人方,分求子、妊娠恶阻、养胎、妊娠诸病、产难、子死胎中、逆生、胞胎不出、下乳、虚损、虚烦、中风、心腹痛、恶露、下痢、淋渴、杂治、补益、月水不通、赤白带下崩中漏下、月水不调二十一类,共五百多方,显示了孙氏在妇科种子、养胎、临产、产后病、经带等方面独到的体会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建立妇女专科思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该书卷八至卷十四是少小婴孺方,分初生出腹、惊痫(附中风)、客忤、伤寒(附寒热)、咳嗽、癖结胀满(附霍乱)、痈疽瘰疬(附丹毒)、杂病九类,共三百多方,内容丰富,论域广泛,集唐以前儿科医学之大成,并有自己的发明创见。孙氏在《备急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序例中指出:“夫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27]由此可见,他对儿科医学的重视。后世认为“少小婴孺方”是中医儿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运用价值。由于《备急千金要方》在妇幼保健工作中的良好作用,长期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还影响到和日本的汉医。约出于明代的《急救仙方》也是一部重要的道教医药学著作,该书前三卷辑明朝徐守贞所撰《妇产急救方集》,言救治妇产科疾病之方,分作妊娠诸疾晶、产难诸疾品、产后诸疾品、妇女杂病品,同样对妇女身心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28] 道门有时也通过服食道符进行妇幼保健。约出于唐宋之《太上说六甲直符保胎护命妙经》以元始天尊和尹喜真人对话的形式提出:世间妇女难产之原因在于“不信至道,不敬,或累业前缘,或今生纵造,不识宿命,不崇正教,信用妖邪,心转迷惑,……临至产时,真神不附,致使邪魅魍魉鬼神妄来干犯”[29]。居于这种神学上的认识,道教符箓道士有针对性地创制了许多安胎、保生、优育符,供妇幼保健使用。如宋代《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下就有许多求子安胎符和产难符,明代《灵宝无量度人上经》中也收录了很多保佑妇女生产平安、促进幼儿智力发育的符文。不可否认,这些护产符、护长符有宗教色彩,但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些道符往往是有针对性的用药汤送服,有经验的道医开出这些方子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起到保健作用的。此外,道符还有“安慰剂”的功效,在古代医护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它们对减轻妇幼罹患疾病时之苦痛有相当的舒缓作用。 综观上文的论析,道教服食养生者以报天地之恩和父母之恩为出发点,高擎尊人贵生之道教旗帜,他们致力于防治瘟病和妇幼保健,对于保障中国古人的生命健康以及提高百姓的生命质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鲜明地展示了道门爱生护生的情怀。 注释: [1]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222-223页。 [2]王明:《太平经合校》,第309页。 [3]王明:《太平经合校》,第613页。 [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53页。 [5]《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7页。 [6]《道藏》第18册,第512页。 [7]《道藏》第20册,第1页。 [8]《道藏》第17册,第224页。 [9]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88页。 [10]《道藏》第18册,第529页。 [11]按,“五福”语出《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谓所好者德也;考终命,谓善终不断夭。 [12]《道藏》第18册,第529页。 [13]王秀芬:《战胜瘟疫做诺贝尔医字奖看20世纪兔疫字进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0期。 [14]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5]《二十五史》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72-173页。 [16]按,尸注、鬼注即结核病。 [17]盖建民:《道教医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89-91页。 [18]《道藏》第33册,第24页。 [19]按,痨瘵之病即肺结核。 [20]王秀菊:《<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传染病证治析要》,《河南中医》1996年第1期。 [21]《道藏》第26册,第208页。 [22]《道藏》第24册,第613-614页。 [23]《道藏》第6册,第343-361页。 [24]《道藏》第4册,第40-42页。 [25]《道藏》第11册,第670-672页。 [26]《道藏》第26册,第96页。 [27]《道藏》第26册,第96页。 [28]《道藏》第26册,第599-620页。 [29]《道藏》第1册,第878-879页。 (《石竹山梦文化节研讨会论文集》,东方出版社200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