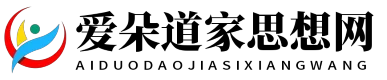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去观察和研究宗教,我们会看到一种现象,即中国各民族的宗教至少由两种不同系统混合组成:一种是在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形成并与本土文化浑然一体的,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巫傩方术等原生性信仰系统;另一种则是形成于异文化环境并在文化传播和涵化过程中融入本土文化的,如佛教、宗教、伊斯兰教等被称为世界或民族宗教的次生性宗教系统。这种现象非常普及,以至于学者们多有提及,但又很少综合讨论,或由于各人信仰、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不同而无法贯通考察。因此,我们平常看到的学术论著多为针对某种或几种宗教的专门研究及比较研究。这类研究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某种或几种宗教信仰形成、发展及现状的系统知识,但其考察大多依赖史料文献的记载及宗教精英的文字表述,而较少关注各种宗教与其信仰群体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信仰群体的宗教认识及相关实践状况。 中国民族宗教研究所面对的史实和事实告诉我们,每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及相关社会文化活动都是在区分或调和不同宗教系统的过程中得以实际运营,其结果也就形成了宗教文化融合现象。历时地看,这种宗教文化融合过程涉及各民族宗教信仰体系中不同成分的形成及互动形态;而共时来看,这个过程又包含同一民族内部不同宗教话语的博弈及折衷、不同民族间宗教要素的渗透及传播等两大方面。笔者曾多次撰文,从不同角度论证说明中国民族宗教研究中外来宗教与地方性信仰习俗乃至社会文化相互融合现象的普遍性,探讨从人类学视角出发进行理论方法创新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近年,相关学界对各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逐渐增多,关注点也比较丰富多样。但是,笔者认为,国内民族宗教主流研究仍然过于偏重研究各民族宗教的独立性及其与各民族认同的排他性关系,而较少关注不同地区和民族起源的宗教信仰在一个民族内部的传播渗透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互动融合现象。目前学界的研究态势,还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各民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也满足不了各民族互动的深入及相关教育导向的需要。因此,本文简要整理宗教文化融合研究的一些新思考,从中国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整体格局、研究战略及具体拓展路径等几个方面再次强调人类学宗教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题一:宗教文化的“区”与“系” 中国在相当于新石器时期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在一定的地理生态范围形成了大规模聚落文化群体。中国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说明,中国古代文化起源分为北方、东方、中原、东南部、西南部及南方等六大区,区内又存在不同系和类型。区是空间概念,用来确定区域性文化的起源及存在范围;系为时间概念,表示区内文化演变的历史过程;而类型则为区域文化中的不同分支,说明区系文化的具体内容。区系类型理论为客观理解不同地区民族文化的性质和历史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动态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苏秉琦、殷玮璋:《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与考古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相呼应,费孝通提出旨在解释中国各民族从古至今互动融合关系的民族走廊理论,其大致内容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形成于北部草原地区、东北山岳森林地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等六个不同地区,历史上通过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等三大民族走廊拉锯、互动并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及其多样的文化传统。 这种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格局理论对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整体特征的认识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分布也有一个六大“区”格局,是不同民族原生性宗教系统产生和发展的空间范围。比如,西北地区的山岳信仰,北方草原地区的敖包、天神信仰,青藏高原的山神、苯教信仰,云贵高原的龙山龙树、巫蛊方术信仰,中原及东北地区的土地神、地仙信仰,东南沿海地区的水神、妈祖信仰等。而从六个区域内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系”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每个民族的本土性宗教文化都沿着不同发展轨迹、在一定历史时期与一种或数种外来宗教融合,从而形成特殊的宗教文化复合体。其中,外来宗教系统往往后来者居上,成为当地民族宗教文化的核心成分,即主体宗教。如果再沿着三条民族走廊考察各民族宗教文化的整体变迁状态,我们又会发现,在历史上各民族拉锯、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制度化宗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化融合格局。 西北走廊的主体宗教是伊斯兰教,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回等10个主要信仰的民族。这些民族大体属于沙漠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也有少量经营绿洲贸易的商人。 藏彝走廊的主体宗教是藏传佛教,有藏、羌、土等诸多信仰民族,他们属于山地、峡谷农耕民及游牧民,都有与山神、灵魂、巫术有关的原始信仰。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及横断山脉沿线山地、峡谷地区各民族本土信仰及社会文化形成互动融合。 南岭走廊的主体宗教为道教,与壮、瑶、苗、水、布依等山地少数民族的本土信仰系统互动融合。他们是河谷稻作、丘陵旱地农耕民,都有各种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以师公道公等为依托的民间巫傩信仰,其神位及仪式与道教有密切联系。 以上是笔者根据民族学、人类学中国文化多元起源及互动融合的理论框架及其学术精神对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状况进行的一个扼要整理。这种整理的学术意义在于能使我们大致搞清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分布及互动融合的整体状况,从“区”的关联角度导出一系列本土性信仰文化形态,而从“系”的关联角度则凸显外来宗教与本土信仰的互动融合过程。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变得具体,其性质和内容也比较容易理解:从宏观的主体宗教,到地方的本土信仰,再到多样形态的信仰习俗,宗教文化的各种形态一目了然,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也就明确起来。 题二:宗教文化的“融合”与“类型” 人类学对中国各民族宗教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普通信教群众的宗教认识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实践与各种专门研究所呈现的状况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完全不同。我们对中国各民族宗教的研究还需要一个贴近民众社会生活实践,从信仰群体自身认识出发设定问题进行研究的层面。这种认识要求我们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定位研究对象和内容。首先,人类学宗教研究关注的信仰群体,既不是哲学关注的普遍意义载体,也不是宗教学所探讨的某种特定宗教原理的提倡者和传播群体,更不限于国学乃至思想史学热衷讨论的、支撑中国从古至今变迁而连续的宗教思想及相关思维形式的文化精英。我们所面对的信仰群体,是地方性宗教传承的建构及传播群体,包括对象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在内的民众意义上的宗教生活实践者。其次,人类学所研究的宗教,不仅是一种与人们的心灵感知及意识状态有关的、观念化象征化的精神形态,也是与社会组织、仪式、人们的生活实践及行为紧密联系的认知和规范体系,还是影响人们审美、情操乃至情绪的精神催化剂,是一种复杂的文化体系。 这种对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界定体现了人类学综合把握的学术理念,把我们对宗教现象的界定范围扩大到了对超自然存在崇拜以外,要求我们充分关注宗教作为文化体系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功用以及与其他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使得人类学不倾向于从事针对某种宗教及其经典、思想、组织、活动的专项研究,不孤立看待宗教文化的不同系统或对其笼统地抽象分析,而是从各民族社会生活实践出发去观察宗教文化的具体状态,并将其与信仰群体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相关联进行研究。作为这一学术追求的必然结果,某个民族内部或几个民族之间不同宗教文化要素的存在形态及互动融合就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正是出于这种学术考虑,人类学宗教研究较少用“宗教”或“某某宗教”来表述研究对象,而更多提及“宗教信仰”或“宗教文化”。很清楚,宗教文化融合是各民族宗教信仰及相关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我们需要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去面对这种现象。 例如,维吾尔族先民有过自然崇拜、部落神崇拜、萨满等本土信仰,中古以后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外来制度化宗教先后传入,在西域不同地区与本土信仰融合,形成早期维吾尔族多样的宗教文化传统。16世纪以后又全面改信伊斯兰教,而其他外来宗教在新一轮融合过程中逐渐衰退、消亡,伊斯兰教成为其宗教文化的主要形式。这种传统一直维持至今,形成现代维吾尔族以伊斯兰教为民族主体宗教的宗教文化传统。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历史剖面进行研究,发现并把握不同时期维吾尔族宗教文化互动融合的内部机理和规律。 西方人类学宗教研究中的文化中介理论告诉我们,一种外来宗教或相关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融合,需要有特殊的中介系统,构成融合途径。找到这个融合途径,就会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外来宗教的融合机理及社会文化作用提供解释学意义上的分析条件。笔者近年提出宗教文化类型说,尝试为宗教文化融合研究提供具体可行的理论视角及方指导。从笔者研究实践举例看,伊斯兰教与维吾尔族本土性文化传承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为地方性宗教文化系统提供与民俗知识及道德规范紧密相关的知识体系。 这里很清楚,同一种宗教在与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体系融合后,会产生具有不同特征的宗教文化复合体。我们可以用抽象度较高的分析概念,客观合理地对这些文化复合体进行比较和分类,从而得出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类型。比如,维吾尔族是知识体系融合型,回族是社会组织融合型。这里的类型,不同于区系类型理论中的类型,也不是普通的事物分类,而是指信仰某种宗教的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传承,在与该宗教互动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突出特征的文化复合体。宗教文化类型是一种宗教文化融合内部机理及规律的分析模式,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有效的学术视角及方支撑。在个案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中,一旦发现并搞清了宗教文化类型,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去捕捉宗教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而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可为比较分类提供学理依据,从而准确把握不同民族宗教文化间的共性或差异。这是笔者根据自身经验总结出的研究路径,还应该有其他不同的拓展途径。 题三:宗教文化的“整体观”与“民族志” 以上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区”与“系”两个概念分析说明了各民族宗教文化发生、发展及互动融合的整体格局,而用“融合”与“类型”诠释了人类学研究的必然目标和有效路径。接下来将要讨论人类学的整体观在把握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关系及互动融合中的应用,以及与展开宗教民族志研究的有关事项。 在中国各民族中发挥宗教文化主体作用的制度化宗教,其传播之广泛,影响之巨大,是其他信仰体系所难以比拟的。作为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主流,这些宗教体系作为大传统的地位不容置疑。鉴于此,我们可以用宗教文化圈概念去整合这些宗教文化大传统的存在及作用范围。这些大规模的宗教文化圈时有重合,并且一个宗教文化圈内还有分层现象,如藏传佛教文化圈里的格鲁派文化层、宁玛派文化层等;道教文化圈里的正一派文化层、全真派文化层等等。接下来,在这些宗教文化圈层之下,还存在大量地方性宗教文化的小传统,我们可以用信仰圈概念整合分析:比如,青藏高原的山神信仰圈,云贵高原的龙山龙树、巫术信仰圈,北方草原地区的敖包信仰圈,中原和东北地区的地仙信仰圈,东南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圈等。以此类推,信仰圈下还可分为各种不同的祭祀圈。 这样一来,我们就依据区系类型、民族走廊等理论,更加自由且合理地展开中国各民族宗教状况的整体分析,为树立民族宗教研究的目标提供学术思想基础。目前中国各民族的宗教文化研究,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及其诸多分支学科都在做,但都各自为营,理论方法和研究目标各不相同;也没有综合研究团队,成果不成规模,问题偏离实际。笔者认为,缺乏民族宗教文化的整体把握和研究战略上的深入考虑,是出现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宗教文化研究的整体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人类学整体视野下的宗教文化研究,应该说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学科领域,我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各民族群众(乃至海外华人华侨)居住生息的所有地区开展宗教民族志调查和挖掘。通观西方人类学宗教研究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品,从进化论的泰勒、弗雷泽,到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俄文斯普里查德、福特斯、格尔纳,再到解释人类学的格尔茨、埃尔克曼,我们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研究路径都不同,有的关注宗教与社会控制,有的关注宗教与文化象征体系,有的关注宗教与人际互动,还有的关注宗教与心理认知,但他们都会聚焦于信仰群体自身所面对的社会文化问题,都研究宗教在一定社会生活环境中与人们的思维、认知、行为及心理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透过宗教现象去发现人类精神及社会发展的规律,考察和分析象征符号及规范体系的建构原理。 为了能够接近或达到这种宗教民族志研究的学术标准,实现在新资料挖掘和新方法开发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要从文化圈到文化层,从信仰圈到信仰层、再到信仰群体的生活实践和社会问题,全面合理地分解细化研究对象,凸显问题以确立主攻目标。通过从宏观到微观,从对象到问题的学术操作,我们就可以得到合理且有问题指向的研究主题。比如,瑶族的村庙祭祀与权威建构、南方山地民族宗教文化的起源与分布,等等。学者们可以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在整体研究战略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分类和限定,最终确定具体对象及研究课题。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能有效展开一系列相关的宗教民族志调研工作。 本文通过对与宗教文化融合研究密切关联的三个专题的分析和评述,阐明了人类学宗教研究视角及理论方法在中国民族宗教研究领域里应具有的学科地位和学术贡献,并针对具体研究路径及研究实施提出了一些意见和看法。强调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人类学宗教研究的本质不是对宗教理论进行形而上学的归纳和解析,而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及相关文化体系的深刻洞察,能为中国各民族宗教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视角、研究资料及方法;第二,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互动融合研究不仅是民族宗教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等相关研究领域的关联课题,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作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