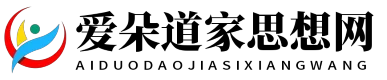尹志华 王安石的《老子注》二卷,《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国史经籍志》均有著录。原书已佚,部分内容散见于金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南宋彭耜《道德真经集注》、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等书中。今人蒙文通、严灵峰、容肇祖均有辑本。蒙文通的《王介甫(老子注)佚文》,原载于四川省立图书馆1948年出版的《图书集刊》第八期。后由其子蒙默重加核校,载于巴蜀书社2001年出版的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一书中。严灵峰的《辑王安石(老子注)》,载于《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中,艺文印书馆1965年出版。容肇祖的《王安石(老子注)辑本》,由中华书局于1979年出版。在以上三个辑本中,严本惟辑彭耜《集注》所引,容本虽辑自李、彭、刘三书,然亦遗漏数条,且误将李霖本人的几处解释系于王安石名下,只有蒙本为迄今为止最完备、准确之辑本。因此,本文主要依据蒙文通的《王介甫(老子注)佚文》来安石的老学思想。 一、道之体乃元气之不动 王安石在《老子注》中,基本上承袭了《老子》以道为本原、从无到有的宇宙生成论。他说,道有本有末,无为道之本,有为道之末。他将《老子》第1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解释为“无,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其终,故曰万物之母。”(P675)因此,道生万物的过程也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王安石认为,从无到有的演变经历了一些中间环节。他说:“无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于太始,自太始至于太极,太始生天地,此名天地之始。有,形之下者也。有天地然后生万物,此名万物母。母者生之谓也。”(P675)这里把天地形成以前的宇宙变化过程分为太初、太始、太极三个阶段,显然是对汉代的《易纬·乾凿度》“五运说”的简化。至于“有天地然后生万物”的说法,则本之于《周易·序卦传》。 王安石对《老子》之“道”的阐释,比较有特色的是以元气为道之体。他解释《老子》第4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说:“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其冲气至虚而一,在大则为天五,在地则为地六。盖冲气为元气之所生,既至虚而一,则或如不盈。”(P680)他又在《老子》第52章的注解中说:“一阴一刚之谓道,而阴阳之中有冲气,冲气生于道。”(P700)可见,王安石认为道之本体是元气,元气含阴阳,从阴阳的运动变化中产生冲气,冲气为道之用。冲气至虚而一,但它在不同的事物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即所谓“在天则为天五,在地则为地六”。这种观点似可概括为“气一分殊”说。王安石完全用气来解释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继承了中国古代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传统。至于他将道之体理解为“元气之不动”,则显然与《周易·系辞传》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说法有关。需要予以辨析的是,王安石既以元气为道之体,却又在《老子》第5章的注释中说:“道无体也,无方也,以冲和之气鼓动于天地之间,而生养万物,如囊禽虚而不屈,动而愈出。”(P681)这两种说法是否矛盾呢?实际上,王安石所谓“道无体也,无方也”是指道没有特定的形体、固定的方所。其思想渊源于《周易·系辞传》中的“神无方,而易无体”的说法。因此,王安石的观点就是:道以元气为本体,但是元气并没有特定的形体和固定的方所。“道以元气为体”与“道无体”,两个“体”字的含义并不相同,因此两个说法并不矛盾。 二、为学穷理,为道尽性 王安石的学术,被他的追随者概括为“道德性命之学”。他的女婿蔡卞说:“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刚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与孟柯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按照这种说法,道德性命之学在宋代的复兴,应该归功于王安石。这似有拔高之嫌,但是,王安石重视对道德性命之理的研究,则是事实。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说:“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探求性命之理,是王安石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也反映在他的《老子注》中。 王安石注《老子》第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说:“为学者,穷理也。为道者,尽性也。性在物谓之理,则天下之理无不得,故曰日益。天下之理,宜存之于无,故曰日损。穷理尽性必至于复命,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者,复命也。然命不亟复也,必至于消之复之,然后至于命,故曰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P699) 王安石的解释,以《周易·说卦传》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观点为主旨。《说卦传》的这句话在宋代获得了高度的重视,成了宋儒所广泛征引的名言,反映了一种时代。 王安石以“穷理”作为“为学”之目的。他所说的理,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如他在《老子》第2章的注释中说:“夫美者,恶之对,善者,不善之反,此物理之常。”(P677)他在第5章的注释中说:“天地之于万物,当春生夏长之时,如其仁爱以及之;至秋冬万物凋落,非大地之不爱也,物理之常也。”(P681)又说:“人事有终始之序,有死生之变,此物理之常也。”(P681)可见,“穷理”就是要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常理”,即客观规律。 王安石认为“为道”的目的在于“尽性”。所谓“尽性”,是指保全和发挥人的天性。他注释《老子》第59章“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啬,是谓早服”说:“夫人莫不有视、听、思。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视而使之明,听而使之聪,思而使之正,皆人也。然形不可太劳,精不可太用。太劳则竭,太用则瘦。惟能啬之而不使至于太劳、太用,则能尽性。尽性则至于命。早复者,复于命也。”(P703)按照王安石的意思,目能视,耳能听,心能思,是人受之于天而具有的能力,可称之为天性。人顺着这种天赋之能力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使视明、听聪、思正。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不伤害人的天赋之性为前提。因此,所谓尽性,就是使自己的天赋能力得到最完善的发挥。 《老子》将“为学”与“为道”二者对立起来,以“为道”排斥“为学”。而《说卦传》关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观点,事实上是将“穷理”、“尽性”、“至于命”置于一种递进的关系中。既然王安石将“为学”解释为“穷理”,将“为道”解释为“尽性”,那么,逻辑的结论就是:为学与为道也是递进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但是,王安石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的说明,而是笔锋一转,以“尽性”消解了“穷理”。他说:“性在物谓之理,则天下之理无不得。”这句话如何理解?“性在物谓之理”,是说人与物皆有天赋的属性,在人则称为人之性,在物则称为物之理。人性与物理皆出于天,其理相同,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理,所以说天下之理无不得。王安石又说:“天下之理,宜存之于无。”其意是说,不能让“穷理”妨碍“尽性”。阅为人之性,因物有迁,只有摆脱外物之牵累,才能尽性,所以对万物之理,应该无所计较而存之于无。王安石在解释《老子》第15章“涣若冰将释”时说:“性本无碍,有物则结。有道之士,豁然大悟,万事销亡,如春冰顿释。”(P689)既然万事消亡,心中当然也不会再计较万物之理。王安石在《致一论》中有两段话,可以加深我们对“天下之理,宜存之于无”的理解。王安石说:“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又说:“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则莫能以惑其心也。”王安石认为,万物各有其理,众人为万理之分殊所迷惑,而圣人则能从万理之中提炼出一个根本的东西,即“致其一”。这个“一”,也就是“道”。韩非子早就说过:“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王安石所谓的“致其一”,也就是以道尽稽万物之理。如果掌握了“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的道理,则不必再从万物具体之理上去穷究,所以说“天下之理,宜存之于无”。王安石说:“穷理尽性必至于复命。”所谓“命”,他在注释《老子》第16章“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时说:“命者,自无始以来,未尝生、未尝死者也。”(P689)可见,王安石所谓的“命”,只有本体的意义。所谓“复命”,就是复归于人的生命本体。而人的生命本体,也就是宇宙之本体,因此,“复命’,就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至于王安石所谓“然命不亟复也,必至于消之复之,然后至于命”,是说复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逐渐消除本性之外的东西,心中之外物消除一分,本性就复一分,这样不断“消之复之”,才能最后至于“复命”。 三、有无同出于道 在有无问题上,王安石反对贵无贱有论,主张有无同出于道。他说:“世之学者,常以无为精,以有为粗,来知二者皆出于道。”(P677) 王安石首先对有无加以界定,他说:“无者,形之上者也。”“有,形之下者也。”(P675)王安石所说的有、无,兼有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意义。从宇宙论角度来说,无是指天地未形成以前的状态,有是指天地生成以后的状态。他说:“无,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其终,故曰万物之母。”(P675)从本体论角度来说,无与有是道的体与用或本与末。他说:“道之本出于无,……道之用常归于有。”(P676)意即道以无为体,以有为用。他又说:“道一也,而为说有二。所谓二者何也?有、无是也。无则道之本,所谓妙者也。有则道之末,所谓徼者也。”(P676)对于本与末、妙与徼,王安石并无重此轻彼之意。他说:“微妙并观,而无所偏取也。”(P676)因为道包含有无二者,有不是道,无也不是道,不能贵无而贱有。 关于有无之关系,王安石说,“有无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故非有则无以见无,而无无则无以出有。有无之变,更出迭入,而未离乎道。”(P676)这段话说明了有无对立统一关系的二层含义:(1)有与无就像东方与与西方那样相反相成,而不是相互否定。(2)由有而见无,由无而见有,有无相互对照。(3)任何事物在变化过程中都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有与无相继替代与变动。最后,王安石强调“有无之变,更出迭入,而未离乎道”。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有无的对立统一关系是道自身的表现,所谓有与无都只是关于道之存在形式的描述而已。 王安石还专门针对《老子》第11章强调“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观点,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老子的意思是:任何有形实体给人带来的益处,必须要靠无形的空间才能发挥作用。王安石则反过来证明:无必须靠有才能起作用。他说:(《老予》)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小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老子以车轮为喻,30根辐条共同连接到中间的车毂,在毂中有可穿车轴的空洞,这样才能使车子发挥作用。毂中的空洞就是无,老子据此而言车之用在于无。王安石认为,老子的说法是片面的。毂辐虽然以其“无”而为车之用,但是毂辐本身则是“有”,只要工匠把毂辐造出来,自然就形成了中间的空洞,也就有了“无”的作用。因此,“无”之用是不能脱离“有”而单独存在的。如果只看到了“无”的作用,而不造毂辐,那么哪来车之用呢?王安石由车之有无进而谈到社会层面的有无。相对于礼乐刑政来说,自然无为就是“无”。但是,如果没有礼乐刑政这些社会规范,而只是一味强调自然无为,那是不可能治理好天下的。因此,王安石强调有无并重论,其现实意义就是批判道家的虚无之道。王安石认为,道家之失在于执本而弃末。而真正的道之大全是兼有本末两个方面的。他说:“道之本,出于冲虚杳渺之际,而其末也,散于形名度数之间。是二者,其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为异,何也?盖冲虚杳渺者,常存于无;而言形名度数者,常存乎有。有无不能以并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P676)按照王安石的观点,道之本虽是一切社会规范的最高合理性依据,但由于它蕴藉于冲虚杳渺之际,既无形可见,也没有具体的规则可以掌握,可以称之为“无”。“无”在层面上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但是,道并不只是有本而已,它还有末,即道之散殊。道之末,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礼乐刑政等具体的社会规范。因此,如果像道家那样,“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真正体道的圣人是上知道本,下察道末。王安石说:“圣人能体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无则足以见其妙,存乎有则足以知其徼,而卒离乎有、无之名也。其上有以知天地之本,下焉足以应万物之治者,凡以此。”(P677)上知天地之本也就是理解形而上的自然天道,下应万物之治也就是推行形而下的礼乐刑政等人道,二者虽有上下本末之别,但就道体而言又是统一的。 四、生万物者无为,成万物者有为 如上所述,王安石在论述有无不可偏废的道理时,已经涉及到了对道家无为说的批判。他还进一步从天道与人道的区别来阐明社会必须有为的观点。他说:“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于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已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故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小言其生万物者。盖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之力之所得与矣。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夫道之自然,又何预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为也。”( P686-687 ) 王安石把道区分为本和末两个方面,道之本生万物,道之末成万物。道生万物是一个自然过程,不需要人力的参与。万物既生以后,如何成就万物,则要靠人力来完成。王安石所说的“成万物”主要是指治理万物。他认为,“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治,圣人者出而治之。”(P682)天生、地成都属于自然之道,即天道。因此,王安石所谓道之本,实际上就是指天道,所谓道之末,实际上就是指人道。天道无须人为而万物自然化生,人道则必须有人之作为来确立其规则。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必须制订礼、乐、刑、政等社会规范。王安石认为,老子屏弃礼、乐、刑、政,而纯任自然无为之道,是只知道之本而不知道之末,即以大道遮蔽了人道,故有“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的弊端。 当然,王安石并不是完全割裂人道与天道的联系。人道的最高境界还是以天道为圭旨。他说:“人道极,则至于天道。”(P690)上的有为也不是任意而为,而是以天道作为参照系,按照天道之自然原则而进行运作。所以他对老子的无为说,又在操作原则层面予以肯定。他注释《老子》第6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说:“天道之体虽绵绵若存,故圣人用其道,未尝勤于力也,而皆出于自然。盖圣人以无为用天下之有为,以有余用天下之小足故也。”(P683)王安石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指垂拱静默式的毫无作为,而是指顺应自然的行为方式。所以他赋予“无为”以极丰富的内涵。他解释《老子》第57章“以无事取天下”说:“然而汤放武伐,亦可以无事乎?曰:然则汤武者,顺乎天,应乎人,其放伐也,犹放伐一夫尔,未闻有事也。”(P702)也就是说,只要是“顺乎天,应乎人”,即使像汤放桀、武王伐纣那样的行为,也是“无为”。按照王安石的观点,判断有为还是无为的标准不是为或不为,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为。所以他特别指出:“然无为也亦未尝不为,故曰‘无为而无小为’。”(P699)又说:“圣人未尝不为也,盖为出于不为。圣人未尝不言也,盖言出于不言。”(P677)所谓“为出于不为”,就是以无为的方式而为。所以他又说:“有为无所为,无为无不为。”(P680)从效果上来说,那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有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而顺应事物发展规律、毫不费力的“无为而为”,则无事而不成。 可见,王安石一方面以人道与天道的区别来说明圣人制订礼乐刑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以人道与天道的一致性来说明行为应该遵循“无为而为”的原则,实际上是对儒道哲学作了一种调和。 五、与时推移,与物运转 《老子》第5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自姓为刍狗。”主张行仁政的儒家多对老子此说进行批评,并认为刻薄寡恩的法家就是老子思想的流变。王安石对《老子》所谓的“不仁”作了辨析,并从中阐发出“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变革思想。 王安石说:“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有爱也,有所不爱也。爱者,仁也。不爱者,亦非不仁也。惟其爱,则不留于爱.有如刍狗,当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箧衍,巾之以文绣,尸祝斋戒,然后用之。及其既祭之后,行者践其首脊,樵者焚其支体。天地之于万物,当春生夏长之时,如其有仁爱以及之:至秋冬万物凋落,非天地之不爱也,物理之常也。” 且圣人之于百姓,以仁义及天下,如其仁爱。及乎人事有终始之序,有死生之变,此亦物理之常也,非圣人之所固为也。此非前爱而后忍,盖理之适然耳。故曰不仁乃仁之至。“(P681) 按照王安石的观点,作为统治者,不能说对百姓愈仁慈愈好,而是应该顺应事物的变化,该爱则爱,不该爱则不爱。因此,天地、圣人表面上的不仁,实际上是至仁。因为真正的“仁”,并不是对事物一成不变的爱,而应该是顺物理之常,“不胶其所爱,不泥其所有。通则用之,与时宜之,过则弃之,与物从之。”(P682)万物有生死,人事有代谢,此皆物之常理,天地、圣人顺应事物的变迁,才会有宇宙间的大化流行,所以,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时过而弃,正是体现了对万物、对百姓的大仁。 王安石认为,圣人不以仁爱累其心,故能“与时推移,与物运转”(P682),根据时代要求而采取适宜的措施。他解释《老子》第38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羲皇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尧舜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汤武也。上义,下德也。或曰:汤武,大圣也,谓之下德,可乎?曰:圣人之所同者,心也;所以有上下者,时也。大圣人者,易地则皆然。”(P697)汤武征伐出于义,义相对于仁来说,属于下德。但是,汤武这样做,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即使把汤武换成羲皇、尧舜,他们也会这样做,所谓“易地则皆然”。历史上羲皇、尧舜、汤武的做法不同,那是时代不同使然,他们的心是相同的。后人不能领会圣人之心意,“专孓孓之仁,而忘古人之大体”(P682),所以迂阔而不通世务。 王安石批评“后之学者专孓孓之仁”而不能“与时推移,与物运转”,显然是在为变法张本。宋初政策以宽仁为主,小尚苛察,延至仁宗、神宗之时,遂至吏治懈怠,积弊丛生。当时的士大夫既对社会危机深感忧虑,又对宋初的宽仁之政深怀留恋。王安石坚决主张变法,所以他要提出“不仁乃仁之至”,斩断对前代的感情依恋,以“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理性精神对前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六、先王不尚贤,亦非不尚贤 儒家提倡“选贤与能”,《老子》则主张不尚贤,二者明显对立。王安石是如何看待尚贤问题的呢?王安石一方面充分肯定尚贤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并认为尚贤不会逻辑地导致民之争兴。他说:“群天下之民,役天下之物,而贤之不尚,则何恃而治哉?夫民于襁褓之中而有善之性,不得贤而与之教,则不足以明天下之善。善既明于己,则岂有贤而不服哉?故贤之法度存,犹足以维后世之乱,使之尚于天下,其有争乎?”(P678>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尚贤在现实社会中确实能导致民之争兴。他说:“夫人之心,皆有贤不肖之别。尚贤,不肖则有所争矣。”(P679)老子看到了尚贤的弊端,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尚贤。王安石认为这是老子“不该不遍,一曲之言也”。(P679)他对老子反对尚贤的出发点作了探讨。他说:“求彼之意,是欲天下之人尽明于善,而不知贤之可尚。虽然,天之于民不如是之齐也。而况尚贤之法废,则人不必能明天下之善也。”(P678)王安石认为老子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状态,即人人都明于善。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当然不需要尚贤来引导人们。但是这样的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不尚贤,则人们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王安石又认为,“老子之所言,形而上者也。不尚贤,则不累于为善。”(P679)其意是说,老子站在形而上的天道的高度,主张纯任自然。尚贤,就是要追求善。而不尚贤,纯任自然,则超越于善恶的对立之上。 王安石试图调和儒家之尚贤与老子之不尚贤的矛盾,提出“先王不尚贤,亦非不尚贤” (P679)的观点。所谓“先王不尚贤”,是说“圣人之心未尝欲以贤服天下”(P678)。所谓“亦非不尚贤”,是说“而所以天下服者,未尝不以贤也”(P678)。明白地说,就是先王有尚贤之迹,而无尚贤之心。 七、圣人无我 王安石认为,现实中存在着各种互相对立的现象,如“有之与无,难之与易,高之与下,音之与声,前之与后,是皆不免有所对”。(P677)但是,他又指出:“惟圣人乃无对于万物。”(P677)圣人为什么能达到无对的境界呢?王安石认为是因为“圣人无我”。他解释《老子》第7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说:“圣人,无我也。有我,则与物构,而物我相引矣。万物,敌我也,吾不与之敌,故后之。”(P683>无我,即放弃自我主体意识,从而不与客体构成对立关系。而一旦抱有自我主体意识,则万物都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因此,要超越主客对立,就必须达到“无我”的境界。 王安石解释《老子》第2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说:“此三者皆出于无我。惟其无我,然后不失己;非惟不失己,而又不失人。不知无我而常至于有我,则不惟失己,而又失人。”(P678)为什么无我反而能不失己、不失人呢?推其意,大概是说,无我则没有人我的对立纷争,彼此和谐共处,故人己两全。有我则人己对立,对立则彼此相损,故人己均失。 王安石的“无我”思想,推其渊源,一是《庄子·逍遥游》的“至人无己”和《齐物论》的“吾丧我”的说法,一是佛教《金刚经》的“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说法。王安石曾精研《庄子》,其《九变而赏罚可言》的著名论文就直接脱胎于《庄子·天道》篇。他又喜好佛教,曾作有《金刚经注》。因此,王安石的“圣人无我”说,反映了佛、道两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王安石提倡“圣人无我”,其上的用意,则是以此来约束帝王,劝其不要刚恒自用,不要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而要能听得进大臣的意见。根据需要来诠释《老子》,是王安石《老子注》的一个鲜明特点。 综上所述,虽然王安石的《老子注》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从中已可以看出其明显的理论创新精神。王安石提出的一些观点,对北宋老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他关于“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观点,成了新学派诸人解《老》的指导思想。他关于有无并重的观点,他对无为与有无的辩证理解,则代表了北宋注《老》者的普遍看法。因此,王安石的《老子注》是中国老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他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发挥,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运用《老子》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2] 《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 [3]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6 },《曾子固讽舒王嗜佛》。 [4] 《司马温公文集》卷l0。 [5] 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第676页,巴蜀书社2001年出版。本文所引王安石《老子》注文,均据此书,后面只随引文注明页码。 [6] 《郡斋读书志·后志》。 [7] 《临川先生文集》卷82。 [8] 《临川先生文集》卷66。 [9] 《韩非子》卷6《解老》。 [10] 《临川先生文集》卷68,《老子》。 (《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